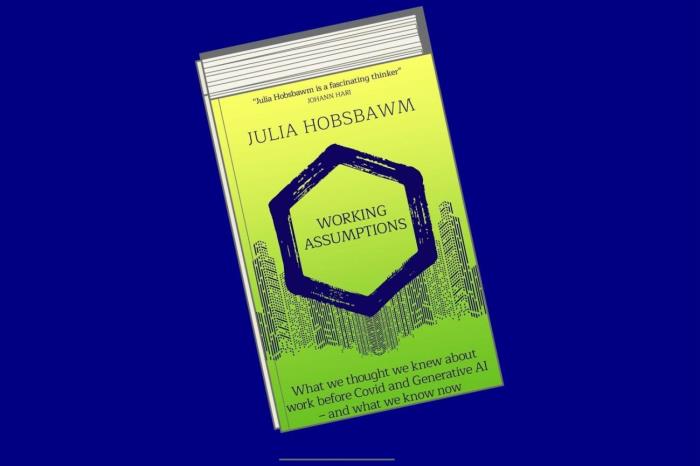通勤“新三角”給商業地產敲響喪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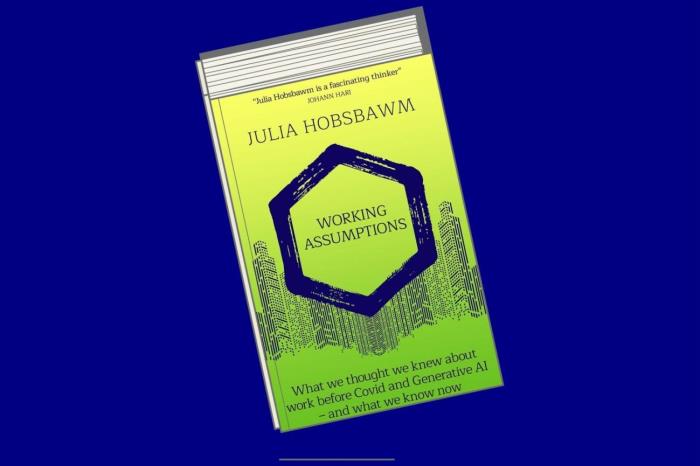 《工作假設》。作者:茱莉亞·霍布斯鮑姆。THE BROWN STUDIO
《工作假設》。作者:茱莉亞·霍布斯鮑姆。THE BROWN STUDIO
時代總是在變。一個世紀以前,福特T型轎車的問世,使得汽車這個東西不再是少數富豪的專寵,1500萬輛T型轎車走進了美國的千家萬戶,它讓人們從此可以跟上時代的腳步,更加自由地探索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這反過來也點燃了更多人的“美國夢”。1936年,當T型轎車即將停產時,美國作家懷特(代表作《夏洛特的網)》這樣評論道:“作為一種交通工具,它勤勞、親民、勇敢。如果你想出門的話,你只需用右手的第三個手指勾住檔位桿,用力向下一拉,左腳用力一踩離合踏板。這些動作簡單而有力,車子就會轟鳴著向前沖。”
別管這臺汽車有多原始,總之它就是能跑起來。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音樂人特蕾西·查普曼憑借一首《快車》(Fast Car)一夜成名。其歌詞充分反映了當時的人們希望通過努力工作過上美好生活的向往。
隨著汽車走進千家萬戶,無數的流行歌曲中都有了它的影子。比如唱失戀不能光唱失戀,要唱“我應該在車底,不應該在車里”。唱奮斗不能光唱奮斗,要唱“握住命運的方向盤”。美國作家邁克爾·康納利寫過一本暢銷書《第五個證人》,主角米基·豪勒又稱“林肯律師”,“林肯”指的就是他的林肯車。他的辦公地點就是在公路上,在他的車里。他的辦公室既無定所,又無處不在——總之,人們總是開著車奔向生計和希望的所在。
對我來說,我的通勤工具也一直是汽車。在上世紀70年代,那時我還生活在倫敦北部的卡姆登,我經常會透過窗子看著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車。當時我的同齡人大都在上大學,而我已經開著車子去工作了。在我21歲生日的時候,我的表姐送了我一輛銀色的豐田花冠,我經常開著它在倫敦四處轉。當時我在倫敦國王大道的企鵝圖書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后來又去了相距不算太遠的英國廣播公司(BBC)工作。當時我對職場的歸屬感還不如我對這臺車子的歸屬感強。在這兩家公司,我做的都是坐辦公室的工作,辦公室是一個相對靜止的空間,有文件柜、有線電話和成堆的紙張。但是汽車卻是動態的,它以一種激動人心的方式,將我帶進了屬于成年人的工作世界。
時代總是在變,我工作過的所有地方也在變。BBC的總部倫敦白城過去又被稱為“電視中心”,它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座巨大的SOHO大樓。企鵝圖書公司的舊址也變成了一幢幢公寓樓。人們開車去上班的習慣也一定程度上發生了改變。現在,開私家車上班就像吸煙一樣,已經成了一個政治性問題,一方面是因為氣候變化原因,加上倫敦的政策鼓勵人們騎自行車,一方面是因為公交系統的發展,還有一方面則是疫情對人們通勤習慣的影響。
現在,汽車本身已經成了一個過時的符號,同時它也在不斷升級換代。現在的汽車跟以前也有了顯著變化,從燃油車到電動車,再到無人駕駛汽車。汽車、通勤與城市,這三者彼此聯系,而且都在持續變化。通勤所依賴的傳統力量,是人們朝九晚五地在城市的某一棟辦公樓里上班。近一個世紀以來,這是無數人早已習慣的生活方式,所有人都這么做,沒有人會對此提出任何質疑。直到這種肉體的、機械的運動被另一種運動所顛覆——即對個人移動化的渴望。
自從手機和互聯網被發明出來,一切都變得不同了。隨著外包和全球化的到來,通勤正在由外在移動向內在移動轉變。現在有100萬美國人已經從北方搬到了南方。而據全球最大的自由職業者網站Upwork預測,隨著遠程辦公革命的興起,將來最終需要“肉身移動”去工作的崗位,可能最多只占全部勞動力的10%。靈活性與流動性是相輔相成的,以Uber為代表的網約車行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了網約車,現在的城市可以運行得很好,但是如果沒有網約車,似乎就沒有那么好了。網約車的例子說明了城市需要一定的時間來適應新的系統,尤其是在科技與人們的工作模式發生沖突的情況下。而Uber也是花了一段時間才醒悟過來,意識到他們需要正確對待工人,給予他們一定的權利和保護。另外在倫敦,Uber極大地沖擊了倫敦非常有代表性的黑色出租車行業。現在這些出租車司機也必須接受刷卡和非現金交易了。出租車司機們對此怨聲載道,但是服務效果確實更好了。
通勤噩夢
很多時候,可能我們更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而不是想要什么。有一件事我們是確信無疑的,那就是通勤是一件所有人都討厭的事,它消耗時間、消耗生命。通勤時間也與一些城市的辦公樓入住率下降有直接關系,因為有些地方光是進城或者出城一趟,就得花費一個多小時。
我們還知道,通勤不僅不受歡迎,而且對人很不健康。雖然在英國,人們開車出行更多是為了購物和休閑,而不是通勤,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卻并非如此,比如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仍喜歡開車上班。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遠程辦公可使碳排放量減少58%。當然,氣候變化也會影響人們對生活和工作地點的選擇。比如在美國,與氣候風險相關的房地產保險雖然有所縮水,但整體規模仍相當于全美GDP的17%。
通勤問題的關鍵,就在于人們如何進入和穿過城市,也就是如何從家移動到單位。不過自從2020年3月,全球進入“居家模式”以來,多數上班族朝九晚五的日子自此告一段落。城市、辦公室和家構成了一組“新通勤三角”,只要技術條件允許,這三者都可以成為打工人的辦公地點。
說一千道一萬,人們對工作場所一般并不挑剔,而更強調以人為本,但是人們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質量還是有要求的。人們現在想要的有三點:第一是更好地實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第二是工作收入能比較輕松地滿足生活成本,第三是有好的技術手段來方便隨時隨地工作。而通勤城鎮將在那些住房和育兒成本合理、供給充足、不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地方發展起來,當然它們離企業總部的距離也不能太遠。
就目前來說,我們有的問題要比答案多。我對工作和職場的看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我在倫敦的所見所聞的影響。倫敦是我生活的地方,而紐約則是我的另一個家,我每年都要在那里工作幾次。在理解通勤問題的總體趨勢上,有一個人給了我很大幫助,他叫彼得·米斯科維奇,是一個紐約人,也是全球領先的商業地產咨詢機構JLL的全球未來工作項目的咨詢負責人。
彼得已經在房地產和工作轉型領域摸爬滾打了20多年,他具有出色的商業天賦,同時也對他的研究領域了如指掌(全球不少知名品牌都是他的客戶),而且他是個非常坦誠的人。他非常實事求是,他是最早證實我的猜測的人之一——即商業地產格局將被新冠疫情永遠改變,而當時很多人并不認可這個觀點。
他對我說:“我傾向于用30年到50年的眼光來看待商業地產乃至整個房地產業,現在我們已經經歷了三四十年的轉型期,而且它現在還在加速,帶來了更多的顛覆性和復雜性。隨著而來的是圍繞供求關系的一個有趣的悖論,人們既關注成本管理,也注重提升人的體驗;既關注整合新的顛覆性技術以實現新的工作方式,也關注大規模的勞動力人口結構變化。所有這些影響因素都在同時深刻影響著今天的商業地產行業。”
“因此,在過去5年里,商業地產板塊的復雜性在急劇增加。我們現在正與幾家全球性客戶合作,研究制定2030戰略。而且我們計劃分成兩個4年戰略來實現,第一階段是2024年到2027年,第二階段是2027年到2030年。”
遠程工作革命
變化的不僅僅是時間——比如通勤時間變長或變短,還有人們的語言。這幾年有不少新詞被造了出來。你聽說過“城市末日循環”嗎?經濟學家阿爾皮特·古普塔還發明了“城市啟示錄”這個詞。阿普塔提醒我說,城市是圍繞現有技術(包括技術的局限性)不斷發展的,比如紐約的劇院區就是圍繞它旁邊的服裝區發展起來的。他還提醒我,現在有一個簡單的成本公式,但是現在對許多寫字樓的租戶來說,這個公式并不劃算。
古普塔教授指出,美國的商業地產租賃成本折合到每名白領員工身上,大約是15000美元。如果你是一家大公司,坐擁上億甚至幾十億資產,那么這點成本對你可能不算什么。但是美國私營企業將近一半的工作崗位由300多萬家小企業創造的。對他們來說,租金的高低就決定了他們能租多大的面積來完成工作。
那么這些因素加起來意味著什么呢?答案是:移動。人們離開城市,遷往郊區或更小的城市。而辦公室和辦公空間的使用模式也在發生變化。我們不應害怕變化,而應當順應變化。通勤和“末日循環”的喪鐘已經敲響,但它同時也會催生一些新的東西。斯坦福大學的尼古拉斯·布魯姆教授曾預言,遠程辦公和混合辦公將成為未來的主流。2023年8月,他在《經濟學人》上撰文稱,“遠程工作的趨勢就像Nike的那個小鉤子標志一樣,疫情以后,起初會有一定下降,隨后會趨于穩定,最后將來會出現長期的大幅增長"。
說起城市商業地產的動蕩,Wework是一個很好的例子。WeWork在2023年底的破產,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那個時代,人們以為傳統的辦公室生活會永遠持續下去,事實證明這是一個代價昂貴的錯誤。WeWork的興衰,象征著辦公室時代的結束——當然實際上,這也只是WeWork的結束(WeWork的創始人亞當·紐曼是一個很有魅力但也很有爭議的人,我個人總是分不清他和知名演員杰瑞德·萊托。紐曼現在正在試圖把Wework買回來。但是我認為,人不能走回頭路,只能向前看。所以我們可以說,WeWork已經停止工作了。)
在2020年以后,全球商業地產市場下跌了20%左右,而且應該永遠也回不到原來的樣子了。2024年1月,美國諮商會發布的一份頗具影響力的報告顯示,全球的CEO們已經開始將吸引人才作為“高關注度”的目標,而將讓員工回到辦公室辦公視為“低關注度”的目標。這一切都表明,對企業來說,在讓員工回辦公室上班的問題,明智的做法是要考慮社會基礎,不強制全時坐班,搞差異化的安排,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搞一刀切。
盡管以WeWork為代表的共享辦公空間模式曾被宣傳為最適合自由職業者的工作模式,而且它也備受那些辦公空間不足,或者想顯得時髦一些的企業青睞,WeWork也一度賺得盆滿缽滿,但是等到它關閉時,它在全球40多個國家的近800個地點的上百萬個工作站已經空空如也。
對于投資者和開發商來說,商業地產已經成了一個“百慕大黑洞”,一些明智的投資者和開發商可能會試水那些工作與生活一體的項目,并且聘請像彼得·米斯科維奇這樣的人才來幫他們設計路徑。但是,現在一個新的“通勤三角”已經出現了,它更強調的是人、家庭與工作的協調共生。它不是一個會讓你迷失的地方,但它也有一系列需要解決的動態問題。現在,一個工作者可能同時坐在家庭生活的中心和工作生活的中心。如果有企業能明白這一點,并認真圍繞他們的職業特點、工作內容和工作空間進行設計,就有可能打動他們、激勵他們,并且幫助他們走得更遠。
摘編自《Working Assumptions: What We Thought We Knew About Work Before Covid and Generative AI—And What We Know Now》一書。作者:Julia Hobsbawm。(財富中文網)
譯者:樸成奎
- 免責聲明
- 本文所包含的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看法,不代表新火種的觀點。在新火種上獲取的所有信息均不應被視為投資建議。新火種對本文可能提及或鏈接的任何項目不表示認可。 交易和投資涉及高風險,讀者在采取與本文內容相關的任何行動之前,請務必進行充分的盡職調查。最終的決策應該基于您自己的獨立判斷。新火種不對因依賴本文觀點而產生的任何金錢損失負任何責任。





 財富中文網
2024-05-06
財富中文網
2024-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