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與爭鳴》全國青年理論創新獎10年回顧|柳亦博:學術研究沒有捷徑可走
作為一本自創刊起就將“與大時代同頻共振與青年學人共成長”作為辦刊使命的學術刊物,《探索與爭鳴》長期以來以發現和扶持青年學人為己任。2013年底,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和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指導下,在上海市社聯黨組的領導下,《探索與爭鳴》編輯部啟動實施了包括“全國青年理論創新獎”在內的一攬子“青年學人支持計劃”,目前這一計劃舉辦學術活動50多場,收到各類來稿5000多篇,100多位青年學人獲獎,近萬名青年學人受益。十年來,這一計劃見證和助力新一代青年學人登上學術舞臺。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以“助力厚植學術的青春力量”為專題,邀請了29位《探索與爭鳴》十年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征文獲獎代表進行專訪,現將訪談發表于此。
本期邀請中國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柳亦博,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和行政倫理學研究。

柳亦博,男,博士/博士后,中國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近年來,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學術專著2部。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中國行政管理》《探索與爭鳴》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聚焦國家治理基礎理論和公共行政本土化理論研究。12篇論文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社會科學文摘》等轉載。入選“復印報刊資料重要來源作者(2019)”、政治學人“學術轉載高影響力學者”。以獨立完成人身份分別獲“第三十五屆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山東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一等獎、二等獎”“第三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征文三等獎”等多項科研獎勵。2019-2023入選山師大東岳學者(青年)。主持國家社科青年項目、濟南市社科重點項目、博士后面上項目等多項課題,擔任《中國行政管理》《探索與爭鳴》《公共行政評論》《行政論壇》《浙江學刊》等多家CSSCI 期刊的外審專家。
澎湃新聞:能不能介紹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內容?
柳亦博:我主要從事政治哲學和行政倫理學研究,這是一個相對小眾的研究領域,主要研究國家治理的基礎理論問題,也會探討一些關于“萬物數字化”和“算法倫理”等問題。包括但不限于探討“國何以為國”的國家理論,探討“國家如何實現良治”的治理理論,以及“國家內部分歧如何解決”的民主理論等,還會涉及到“合作的建立”“信任的形成”“共同體的秩序”“算法倫理”“人工智能”等。我想,可能我屬于以賽亞·柏林說的那種“狐貍型學者”,狐貍知道很多事情,他的思維是由中心向外發散的,可以同時討論多個話題。
澎湃新聞:您能向我們介紹一下您的學術經歷嗎?您認為自己在學術上取得進步的主要經驗和體會是什么?
柳亦博:我是在碩士階段正式進入行政學專業的,當時跟隨導師做公共政策分析,后來讀博士期間逐漸轉型從事我更感興趣的規范研究。印象中開啟我公共行政學規范研究之路的第一本書是法默爾的《公共行政的語言》,起初我自己學術積累不夠,完全看不懂法默爾在說什么,只能先硬著頭皮讀下去,不懂的地方先略過,等以后再回來返工。這個過程當然很折磨,幸運的是很快隨著我在政治哲學和倫理學方面閱讀量的提升,很多過去困擾我的難題一下子消失了,我仍記得當我發現自己突然能讀懂《公共行政的語言》時的那份驚喜,仿佛自己一下子找到了修煉絕世武功的“秘籍”。當然,想要在今天的學術界生存下來,只靠能讀懂文獻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有足夠亮眼的發表記錄。說到學術發表,我個人的經驗是,多讀多寫是提高學術寫作能力的唯一方法,沒有其他任何捷徑可走。
澎湃新聞:在您的學術生涯中,遇到過哪些困難?您覺得對于青年學者來說,哪些方面的幫助是很重要的?在您的學術成長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經歷對您有重要影響和幫助?
柳亦博:我想,對于今天在學術發表里“卷來卷去”的多數學者而言,大家的學術經驗和體會應該是趨同的,即目前被各大高校和科研單位納入“有效科研名單”的學術期刊太少,它們遠遠無法消化掉所有的學術論文產出。在這樣的背景下,勤奮刻苦的價值在不斷下降,天賦和師承的意義則不斷提高。上世紀90年代的那種依靠引介某位西方學者的思想,或者翻譯一本著作就能名利雙收的好事早已沒了,甚至本世紀初流行的融西方學說進中國現象、著書立說變成知名學者的奮斗經驗,于今天的青年學者而言多半也已失效。所以,對于青年學者來說最重要的幫助是給他們一個能夠持續發聲的穩定平臺,只有他們的聲音被聽到,才有交流、爭鳴和進步的空間。青年學者不是也不必是苦行僧,他們普遍處在一個人生多重壓力呈疊加態的階段,婚戀、生育、購房、職稱晉升、論文發表、課題申報、學術評獎,以及教學課時量、講座與學術會議、學生指導等等事務的考核,逼迫著大多數青年學者不得不有所取舍,所以高知分子晚婚晚育已是常態。從我個人的經驗來講,2019年初獲得《探索與爭鳴》雜志社的“第三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征文”獎,對于那時的我而言無疑是一劑強心劑,讓我倍感鼓舞的同時,忐忑緊張的心態也松弛了下來。很快我就在19年和20年,分別獲得了山東省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和一等獎,以及“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作者”和“青年東岳學者”的榮譽稱號,又在21年獲得了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雖然我沒做詳盡的統計,但在政治學和公共管理領域我是近幾屆最年輕的一等獎獲得者)。回望來路,我想之所以我能在19年之后連續獲獎,與《探索與爭鳴》雜志社給我的學術自信有很大關系,所以我一直對雜志社充滿感激,是《探索與爭鳴》在我迷茫的時候第一個伸手拉了我一把。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青年學者,您覺得當下的學術氛圍是如何促進您個人的研究的?
柳亦博:我并不認為當下的學術氛圍是有益于學術研究的,至少于我個人而言,現在的學術界顯然過于功利、過于急躁了。以政治學和行政學為例,知網可檢索到的這兩個學科的文獻中,我認為至少80%可被歸為“學術泡沫”,它們催生了學術界的虛假繁榮,但這些文章真正的知識貢獻幾乎為零。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先改革學術考核機制。
澎湃新聞:面向青年學者有不少相關的扶持政策,這些政策對您的學術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幫助?
柳亦博:的確如此,一方面我是青年扶持政策的受益者,我拿到了一些面向青年的專項課題,也獲得了青年的學術獎勵。但另一方面,隨著不斷迫近這些政策要求的年齡邊界,我也深切的感受到自己被焦慮所籠罩,擔心自己過去的成績其實是源于學術界對青年的保護。實話實說,對于失去了保護殼還能否在學術叢林中生存下去這個問題,我并無十足把握。
澎湃新聞:您認為您所開展的哪些課題研究及其成果,對您獲得《探索與爭鳴》全國青年理論創新獎有所助益?
柳亦博:我獲獎的論文是《話語體系與“環世界”:現代國家治理的正典敘事與話語重構》,這篇論文是非常典型的規范研究,探討的也是非常基礎的理論問題。在學術界充斥大量實證研究的今天,《探索與爭鳴》編輯部對基礎理論研究的關注就顯得尤為難能可貴。
澎湃新聞:您所開展的學術研究,與當下的社會現實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系?
柳亦博:政治學與行政學都是緊密聯系社會現實的學科,它們研究目的都在于創造一種更美好、更公平、更人性的公共生活,二者唯一的不同只是在研究視角上存在差異。我所開展的研究,多數情況下是跨越這兩個學科的,會對社會現實進行形而上的反思。
澎湃新聞:在強調“學術未來感”的當下,您所開展的學術研究如何做到結合當下,放眼未來?
柳亦博:政治哲學與行政倫理學,是很容易與人工智能碰撞出思想火花的,尤其是行政倫理學,它與人工智能的交叉其實不亞于科技倫理。這是因為,現代公共領域已經進入了高度復雜、高度不確定的階段,決策的復雜性大大超出了人腦的算力極限,所以大量的日常事務不得不借助人工智能去處理。在這樣的背景下,行政部門就會經常遭遇各種算法引至的倫理困境,亟需從事行政倫理學研究的學者們積極回應這些時代難題。
澎湃新聞:獲得《探索與爭鳴》全國青年理論創新獎,對于您的課題研究會有哪些助益?這一獎項對您的學術生涯的展開會有哪些助益?
柳亦博:這個問題我在前面的回答中已經基本覆蓋了。這項獲獎對我學術生涯的開展意義重大。
澎湃新聞:您對于未來有志于參與《探索與爭鳴》全國青年理論創新獎的青年學者有何寄語?
柳亦博:希望所有有志于參與的青年學者,勇敢地發揮學術想象力,勇敢地探索那些未知又有趣的問題,不要畏懼“犯錯”和“嘲諷”,因為這恰恰說明我們正在遠離已有的道路,走上一條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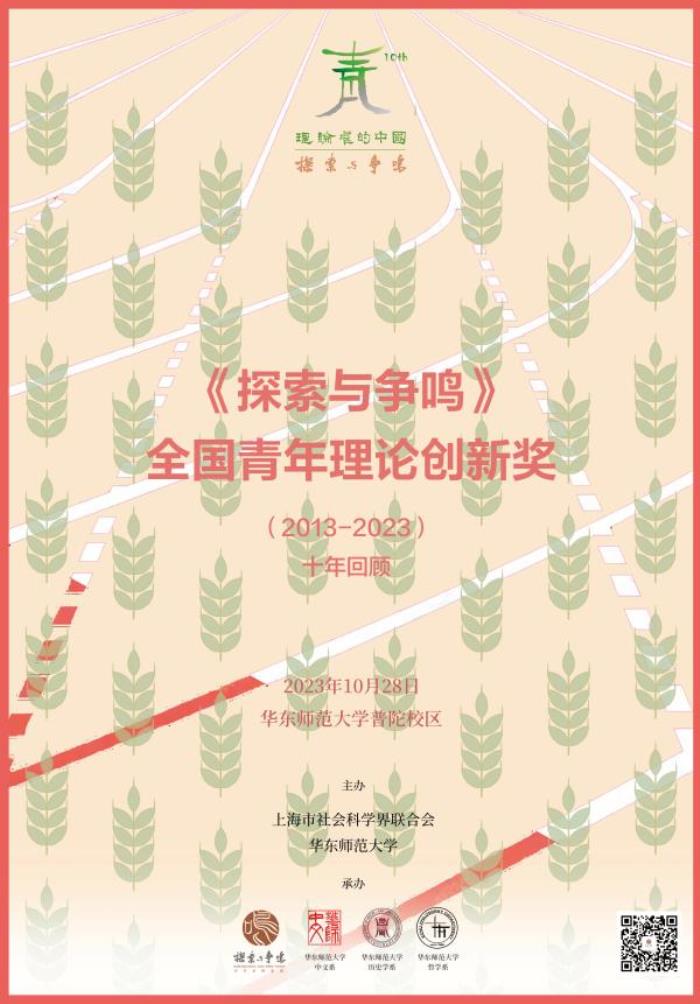
- 免責聲明
- 本文所包含的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看法,不代表新火種的觀點。在新火種上獲取的所有信息均不應被視為投資建議。新火種對本文可能提及或鏈接的任何項目不表示認可。 交易和投資涉及高風險,讀者在采取與本文內容相關的任何行動之前,請務必進行充分的盡職調查。最終的決策應該基于您自己的獨立判斷。新火種不對因依賴本文觀點而產生的任何金錢損失負任何責任。





 新火種
2023-11-03
新火種
2023-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