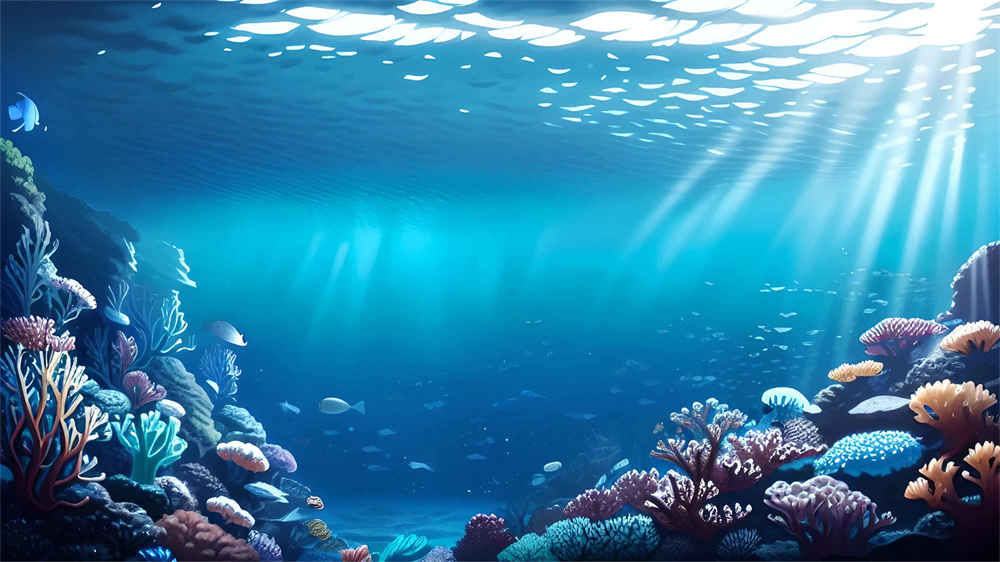深度城市化關(guān)鍵:從“單打獨(dú)斗”走向開(kāi)放協(xié)作
編 者 按
在產(chǎn)業(yè)發(fā)展上既不能“走脫實(shí)向虛的路子”,更需要摒棄經(jīng)濟(jì)“虛實(shí)”分立的有關(guān)傳統(tǒng)觀念,而是要走向“虛實(shí)結(jié)合”、 三次產(chǎn)業(yè)深度融合、產(chǎn)業(yè)鏈上下游相互賦能,最終形成大中小企業(yè)共生共贏的發(fā)展格局

圖片來(lái)源/ 網(wǎng)絡(luò)
文 | 張國(guó)華
城市化是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的必由之路,無(wú)論是塑造一二三產(chǎn)深度融合的現(xiàn)代化產(chǎn)業(yè)體系還是構(gòu)建國(guó)際國(guó)內(nèi)雙循環(huán)新格局,無(wú)論是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設(shè),還是鄉(xiāng)村振興和城鄉(xiāng)融合,無(wú)論是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還是共同富裕之路,發(fā)展模式亟需從“有沒(méi)有”轉(zhuǎn)型“好不好”,從“單打獨(dú)斗”走向“合作協(xié)作”, 這正是推進(jìn)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和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的關(guān)鍵所在。
這需要探索推進(jìn)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和城市化的深層邏輯,在新發(fā)展階段上,探索和構(gòu)建新發(fā)展的深層邏輯,關(guān)鍵在于解決四組關(guān)系的新認(rèn)知,那就是:(1)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jì)體系構(gòu)建中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jí)、打造中高端產(chǎn)業(yè)集群和實(shí)現(xiàn)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業(yè)和人”這組關(guān)系的新認(rèn)知;(2)城市化高質(zhì)量發(fā)展、鄉(xiāng)村振興和城鄉(xiāng)融合的“城和鄉(xiāng)”關(guān)系的新認(rèn)知;(3)城市群和都市圈發(fā)展需要什么樣高品質(zhì)的居住和高效率的出行,“住和行”關(guān)系的新認(rèn)知;(4)在體制機(jī)制保障方面,政府如何更好發(fā)揮作用和市場(chǎng)怎么樣發(fā)揮決定性作用,“政府和市場(chǎng)”這組關(guān)系的新認(rèn)知。
業(yè)和人的新認(rèn)知
對(duì)外開(kāi)放和“虛實(shí)融合”是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jí)的關(guān)鍵,不同類型的就業(yè)人口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是共同富裕的根本出路。
首先看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jí)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隨著經(jīng)濟(jì)全球化進(jìn)程的日趨加快,各種要素的流動(dòng)速率加快、融合程度加深、關(guān)聯(lián)效應(yīng)加大。在產(chǎn)業(yè)升級(jí)方面,只有將勞動(dòng)力從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到生產(chǎn)效率更高的制造業(yè)和服務(wù)業(yè)部門,才能帶來(lái)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的根本提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數(shù)量級(jí)效應(yīng)成為基本特征。在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方面,產(chǎn)業(yè)間協(xié)同的逆向帶動(dòng)作用日益重要,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越來(lái)越依賴于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部門所提供的肥料、農(nóng)業(yè)機(jī)械、物流配送、倉(cāng)儲(chǔ)設(shè)備乃至金融服務(wù);制造業(yè)的高端化和競(jìng)爭(zhēng)力提升相當(dāng)程度上取決于能否獲得低成本、高質(zhì)量的生產(chǎn)性服務(wù)賦能,而生產(chǎn)性服務(wù)業(yè)是從制造業(yè)產(chǎn)業(yè)細(xì)分中逐漸剝離出來(lái)的。沒(méi)有高度發(fā)達(dá)的生產(chǎn)性服務(wù)業(yè),就沒(méi)有高度發(fā)達(dá)的工業(yè),更沒(méi)有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農(nóng)業(yè)。
德國(guó)工業(yè)的強(qiáng)大,在于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中占70%服務(wù)業(yè)中有“70%”的為生產(chǎn)提供服務(wù)的服務(wù)業(yè);美國(guó)國(guó)家的強(qiáng)大,在于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中占80%服務(wù)業(yè)中有“80%”的為生產(chǎn)提供服務(wù)的服務(wù)業(yè);這需要我們?cè)诋a(chǎn)業(yè)發(fā)展上既不能“走脫實(shí)向虛的路子”,更需要摒棄經(jīng)濟(jì)“虛實(shí)”分立的有關(guān)傳統(tǒng)觀念,而是要走向“虛實(shí)結(jié)合”、 三次產(chǎn)業(yè)深度融合、產(chǎn)業(yè)鏈上下游相互賦能,最終形成大中小企業(yè)共生共贏的發(fā)展格局。
其次,從我國(guó)產(chǎn)業(yè)全球化現(xiàn)實(shí)歷程來(lái)看,在上個(gè)世紀(jì)90年代,以IT和汽車為代表的中高端產(chǎn)業(yè)上是美、日、歐三分天下,那時(shí)候還沒(méi)有中國(guó)人的事;在新世紀(jì)的第一個(gè)十年,我們看到的是“中國(guó)出口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jī)”;但在第二個(gè)十年,我國(guó)在全球貿(mào)易體系中正從以“服裝鞋帽”為主導(dǎo)的中低端產(chǎn)品向以“IT、汽車和機(jī)電”為主導(dǎo)的中高端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在加入WTO特別是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中國(guó)手機(jī)品牌從2020年以來(lái)已經(jīng)占全球份額的40%以上,汽車在今年上半年超越日本已經(jīng)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guó),這才是中國(guó)過(guò)去二三十年整個(gè)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來(lái)龍去脈,因此,不斷擴(kuò)大的對(duì)外開(kāi)放的深度和廣度、高度參與全球產(chǎn)業(yè)鏈和價(jià)值鏈的分工協(xié)作、產(chǎn)業(yè)升級(jí)沿著供應(yīng)鏈從下端向上端的持續(xù)轉(zhuǎn)型,才是我國(guó)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jí)的根本動(dòng)力所在。
落實(shí)好“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xiàn)代化”的目標(biāo),這需要從抽象的“人民”回歸到具象的“人”的新認(rèn)知,亟需結(jié)合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一二三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口的變化態(tài)勢(shì)來(lái)分析和認(rèn)知具象的“人”,解決好就業(yè)人口的科學(xué)認(rèn)知。
進(jìn)入現(xiàn)代化國(guó)家的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普遍規(guī)律都呈現(xiàn):農(nóng)業(yè)占GDP的比重1%-3%,農(nóng)業(yè)就業(yè)人少、生產(chǎn)率高,1%的農(nóng)業(yè)就業(yè)人口搞1%的農(nóng)業(yè)GDP,這是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的一個(gè)基本特征;而這些國(guó)家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發(fā)展歷程都呈現(xiàn)了農(nóng)業(yè)GDP占比、農(nóng)業(yè)就業(yè)占比同步雙下降。而我國(guó)過(guò)去四十年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發(fā)展中雖然也上呈現(xiàn)了農(nóng)業(yè)GDP占比和農(nóng)業(yè)就業(yè)占比雙下降,但當(dāng)下我國(guó)農(nóng)業(yè)占GDP的比重6%,農(nóng)業(yè)就業(yè)人口將近30%,30%人才搞了個(gè)6%GDP,經(jīng)濟(jì)效率是不會(huì)高的,這樣的狀態(tài)也無(wú)法解決好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業(yè)就業(yè)人口的現(xiàn)代化。
進(jìn)入現(xiàn)代化國(guó)家的制造業(yè)就業(yè)人口和比例都呈現(xiàn)了雙下降的態(tài)勢(shì)。比如美國(guó)制造業(yè)勞動(dòng)人口比例在1953年達(dá)到30%的頂峰,到2015年,這一比例已下降到10%,英國(guó)則降至12%時(shí),作為制造業(yè)強(qiáng)國(guó)的德國(guó),工業(yè)就業(yè)人口高居現(xiàn)代化國(guó)家或者地區(qū)之首,達(dá)到21%(萊曼,2018)。作為世界上工業(yè)體系最健全的中國(guó)一些地區(qū)也在發(fā)生類似的變化,比如七普和六普相比,廣州市制造業(yè)崗位已經(jīng)從38%降低到20%了,成都市從2009年的31%降低到了2020年的28%。在我們特別強(qiáng)調(diào)以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為支撐的現(xiàn)代化產(chǎn)業(yè)體系建設(shè)和穩(wěn)就業(yè)的大形勢(shì)下,更需要清醒的看到,如何從中低端制造業(yè)轉(zhuǎn)向中高端制造業(yè),需要向日本特別是德國(guó)學(xué)習(xí),那就是需要營(yíng)造高度重視制造業(yè)的生態(tài)氛圍、特有的支持獨(dú)角獸或者隱形冠軍企業(yè)發(fā)展的區(qū)域金融體制、雙元職業(yè)教育體系以及勞資共商共治的合作機(jī)制。
這四個(gè)方面是有機(jī)統(tǒng)一的整體,不能分開(kāi)來(lái)看。寄希望于吸收其中一項(xiàng)特點(diǎn),而不顧及其他方面,都會(huì)導(dǎo)致扭曲的政策效果,這是塑造中高端制造業(yè)崗位的“牛鼻子”所在。
在服務(wù)業(yè)就業(yè)人口變化方面,無(wú)論是從國(guó)家還是地區(qū)來(lái)看,特別是以“紐約、倫敦、巴黎和東京”為代表的世界級(jí)城市主導(dǎo)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呈現(xiàn)了以“科技、金融及專業(yè)化服務(wù)等高端生產(chǎn)性服務(wù)業(yè)”就業(yè)人口和以“保姆、清潔、門衛(wèi)和餐飲服務(wù)等基礎(chǔ)性服務(wù)業(yè)”就業(yè)人口“雙快速”持續(xù)增長(zhǎng),可以說(shuō)服務(wù)業(yè)就業(yè)人口才是這些地區(qū)過(guò)去20年-30年人口就業(yè)快速增長(zhǎng)的主體。在我國(guó)現(xiàn)代化城市治理體系的構(gòu)建中,對(duì)這兩部服務(wù)業(yè)人口存在一定的認(rèn)知偏差,比如,一些主要地區(qū)圍繞科技創(chuàng)新和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jì)體系的發(fā)展目標(biāo)提出了要吸引集聚高端人才,還有個(gè)別城市在治理城市中出現(xiàn)了疏解“低端”人口的聲音,“高端”人才應(yīng)該對(duì)應(yīng)于高端生產(chǎn)性服務(wù)業(yè)人口,而“低端”人口則對(duì)應(yīng)于基礎(chǔ)性服務(wù)業(yè)人口,對(duì)于“高端”與“低端”人口無(wú)疑是我國(guó)城市化進(jìn)程中需要重點(diǎn)認(rèn)知的關(guān)鍵問(wèn)題。
從產(chǎn)業(yè)來(lái)看,消費(fèi)型乃至基礎(chǔ)性服務(wù)業(yè)和生產(chǎn)型服務(wù)業(yè)的關(guān)系是相輔相成的,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源自于市場(chǎng)的發(fā)達(dá),發(fā)達(dá)的市場(chǎng)則意味著市場(chǎng)中有高層次的消費(fèi)需求,而這些需求往往來(lái)自從事高端服務(wù)業(yè)的人群,這些人群不但產(chǎn)生消費(fèi)需求,還為基礎(chǔ)性服務(wù)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人才智慧,這同時(shí)也提高基礎(chǔ)性服務(wù)業(yè)的職業(yè)能力和收入保障,形成閉環(huán)。
此外,對(duì)于從事中高端服務(wù)業(yè)的人群,他們的成就很多時(shí)候并不只取決于工作的八小時(shí)之內(nèi),而在八小時(shí)之外。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閑暇出智慧,自由出智慧,這才是城市作為經(jīng)濟(jì)引擎和創(chuàng)新之源的所在。從城市發(fā)展過(guò)程中,“高端”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和“高端”人口的使用,不僅不會(huì)打壓“低端”產(chǎn)業(yè),反而會(huì)內(nèi)生出對(duì)“低端”就業(yè)的旺盛需求。如同一個(gè)生機(jī)勃勃的魚塘,有各種層次不同的魚混養(yǎng),上層魚吃浮游生物、中層魚吃水藻,下層魚吃上中層的糞便,各層魚因各得其所而相安無(wú)事。這種結(jié)構(gòu)就能很好的保持水體的凈化作用,水塘就會(huì)產(chǎn)生自潔能力。一個(gè)“充滿活力、煙火氣滿滿”的大城市應(yīng)該是海納百川的城市。
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服務(wù)業(yè)才是解決就業(yè)的關(guān)鍵所在,同等重視高端生產(chǎn)性和基礎(chǔ)性服務(wù)業(yè)人口的發(fā)展,才是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與共同富裕的關(guān)鍵抓手,也是穩(wěn)就業(yè)的主戰(zhàn)場(chǎng)。
“城和鄉(xiāng)”的新認(rèn)知
鄉(xiāng)村振興的基本規(guī)律是把鄉(xiāng)村做小,把城市做大,城市是鄉(xiāng)村振興的動(dòng)力,路徑在于城鄉(xiāng)融合。
歐洲特別是西歐國(guó)家在城市化、工業(yè)化和鄉(xiāng)村振興、城鄉(xiāng)融合方面走出了一條值得我們關(guān)注的道路,瑞士蘇黎世鄉(xiāng)村振興道路是,設(shè)計(jì)一個(gè)具有高效便捷的交通系統(tǒng),從而實(shí)現(xiàn)鄉(xiāng)鎮(zhèn)區(qū)域和中心城區(qū)服務(wù)與文化區(qū)域的高效連接,并且是改善貧困地區(qū)狀況和提升鄉(xiāng)村振興整體生產(chǎn)率最簡(jiǎn)單、最便宜的方式。
蘇黎世經(jīng)驗(yàn)背后的深層邏輯是:(1)首先應(yīng)該通過(guò)城市更新行動(dòng),在城市中心區(qū)發(fā)展出鄉(xiāng)村振興所需要的高端生產(chǎn)性服務(wù)業(yè)乃至文化產(chǎn)業(yè);(2)其次,通過(guò)高效的交通系統(tǒng)建設(shè),把鄉(xiāng)村振興地區(qū)和城市中心區(qū)建立高效的連接;(3)通過(guò)鄉(xiāng)村振興行動(dòng)將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空間做好,使“城和鄉(xiāng)”雙向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文化要素自由流動(dòng)和支撐。這三項(xiàng)工作之間相輔相成,互相成就。
城市作為鄉(xiāng)村振興的引擎和動(dòng)力所在,才是鄉(xiāng)村振興和城鄉(xiāng)融合的本, “城和鄉(xiāng)”需要如何從封閉、對(duì)立走向開(kāi)放和協(xié)作?制約瓶頸何在?無(wú)疑是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道路上的戰(zhàn)略挑戰(zhàn)之一,這需要在城鄉(xiāng)融合的改革中破局。
在“城和鄉(xiāng)”的關(guān)系方面,需要從封閉、對(duì)立,走向開(kāi)放和協(xié)作,城鄉(xiāng)融合的關(guān)鍵是一二三產(chǎn)業(yè)深度融合。在“城和鄉(xiāng)”空間協(xié)同方面,關(guān)鍵是盡快以土地為代表的經(jīng)濟(jì)要素流動(dòng)改革。按照“把城做大,把鄉(xiāng)做小。城市才是創(chuàng)造GDP的地方,創(chuàng)造財(cái)富的地方。”的新認(rèn)知,持續(xù)深化城鄉(xiāng)融合建設(shè),縱深推進(jìn)農(nóng)村產(chǎn)權(quán)制度和要素市場(chǎng)化配置改革,通過(guò)現(xiàn)代化的基礎(chǔ)設(shè)施將城市的高端需求和鄉(xiāng)村高效鏈接起來(lái),帶動(dòng)鄉(xiāng)村地區(qū)的發(fā)展,并且產(chǎn)生新的消費(fèi)空間。
“住和行”的新認(rèn)知
都市圈一體化的根本是長(zhǎng)距離+高效率的出行。
在傳統(tǒng)城市的認(rèn)知中,通常在“職住平衡”的目標(biāo)下訴求城市的“小而美”,希望城市通勤距離短,比如國(guó)內(nèi)超大城市的通勤距離通常在10公里左右,北京最高,平均通勤距離達(dá)到了11.7公里,平均通勤時(shí)間為47分鐘。怎么樣評(píng)價(jià)這樣的時(shí)空距離呢?需要基于都市圈乃至城市群和現(xiàn)代城市的新認(rèn)知來(lái)看。
英國(guó)最新的國(guó)家調(diào)查表明,倫敦城市1972年人均出行時(shí)耗為58分鐘,日均出行距離為19.7公里;到2019年,人均出行時(shí)耗為60.8分鐘,較1972年僅增長(zhǎng)了不足4.6%,但日均出行距離達(dá)到了28.7公里,較1972年增長(zhǎng)了45.7%;東京都市圈的通勤半徑從1978年的30公里擴(kuò)展到2018年的50公里,時(shí)間距離從41分鐘擴(kuò)展到了47分鐘。這樣的時(shí)空指標(biāo)變化反映了什么樣的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體系態(tài)勢(shì)呢?首先英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辛普森研究證明了高技能勞動(dòng)力通常會(huì)在更大范圍內(nèi)尋找與自己相匹配的就業(yè)崗位,雖然這會(huì)帶來(lái)了更長(zhǎng)距離的通勤和時(shí)間,但其回報(bào)是更高的工資水平。
《智慧社會(huì)》一書針對(duì)現(xiàn)代城市發(fā)展態(tài)勢(shì)作出了進(jìn)一步闡述,那就是隨著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到來(lái),城市由商品交換主導(dǎo)轉(zhuǎn)向思想交流主導(dǎo),一個(gè)城市創(chuàng)新的效率和能力、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程度、創(chuàng)新創(chuàng)意的業(yè)態(tài)發(fā)展,主要取決于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者在這個(gè)城市里可以探索的距離和頻率,可以訪問(wèn)的不同區(qū)域的數(shù)量大體確定了人們探索的步伐,并進(jìn)一步確定了創(chuàng)新和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的步伐;并且也反面論證這一點(diǎn),那就是以北京為例,北京事實(shí)上被分割成了很多的“小城市”,這影響了北京城市在創(chuàng)新經(jīng)濟(jì)方面的發(fā)展。所以在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出行距離的長(zhǎng)不是問(wèn)題,而是如何提高出行的效率,如何減少出行的時(shí)間,構(gòu)建好長(zhǎng)距離+高效率的交通出行服務(wù)體系,才是都市圈和城市群一體化的關(guān)鍵所在。
談“行”就不能離開(kāi)“住”,居住問(wèn)題最根本在于用地,特別需要解決好城鄉(xiāng)居住用地使用的新認(rèn)知。
全國(guó)國(guó)土空間“三調(diào)”已經(jīng)公布數(shù)據(jù),首先是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鄉(xiāng)村建設(shè)用地占比過(guò)高,鄉(xiāng)村人口持續(xù)減少,鄉(xiāng)村建設(shè)用地持續(xù)增加,全國(guó)農(nóng)村人口占總?cè)丝趧倓傔^(guò)1/3,但村莊用地占到了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的2/3;農(nóng)村人口大量轉(zhuǎn)移到城鎮(zhèn),農(nóng)村建設(shè)用地不減反增。
2020年,全國(guó)鄉(xiāng)村常住人口5.10億人,比2010年減少了1.64億人。但從2009年到2019年,村莊用地面積凈增加346萬(wàn)公頃以上,增幅達(dá)到18.8%,占同一時(shí)期全國(guó)建設(shè)用地凈增加面積的40%以上。村莊用地不僅基數(shù)大,而且成為新增建設(shè)用地第一大戶。顯然,我們就居住用地而言,真正的浪費(fèi)在鄉(xiāng)村,而不是在城市。
然后看城市,關(guān)鍵是工業(yè)用地和居住用地的配置關(guān)系,2017年,中國(guó)城鎮(zhèn)用地中居住用地比例為31.4%,明顯低于美國(guó)的46.9%、日本的61.3%;工業(yè)用地比例為18.5%,明顯高于日本的7.7%、韓國(guó)的10.1%。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這些城市,居住用地占整個(gè)城市建設(shè)用地通常都是50%以上。我國(guó)主要大城市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設(shè)用地比例鮮有超過(guò)30%,深圳最近提出了提高居住用地占建設(shè)用地的比例,北京則進(jìn)一步明確了到2035年提高到39%—40%的目標(biāo)。
中財(cái)辦原副主任楊偉民強(qiáng)調(diào)城市居住用地的嚴(yán)重失衡是導(dǎo)致職住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職住失衡才是交通擁堵的根本原因,因而解決交通擁堵等大城市病的治本之策是調(diào)整空間結(jié)構(gòu),促進(jìn)職住平衡。
所以就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來(lái)說(shuō),以通勤距離所代表的“行”不是大了,是不夠大,以居住用地所代表的“住”不是多了,是少了。在“住和行”新認(rèn)知下落實(shí)要求,特別是總書記在中央財(cái)經(jīng)委員會(huì)第五次、第六次會(huì)議重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為主要承載的優(yōu)勢(shì)空間已經(jīng)凸顯,要圍繞這個(gè)優(yōu)勢(shì)空間去構(gòu)建高質(zhì)量的動(dòng)力系統(tǒng)。這意味著絕對(duì)不能僅僅只從技術(shù)、學(xué)術(shù)角度出發(fā),而應(yīng)該從國(guó)家如何構(gòu)建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體系的角度來(lái)思考,以多層次軌道所代表的現(xiàn)代化高效率出行服務(wù)和高品質(zhì)居住空間在都市圈和城市群的重新配置,探索軌道上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發(fā)展新邏輯,把以優(yōu)質(zhì)中小學(xué)教育和醫(yī)院為代表的公共服務(wù)業(yè)、以市域市郊鐵路為代表的區(qū)域軌道交通建設(shè)和高品質(zhì)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作為外圍新城新區(qū)的發(fā)展杠桿與投資機(jī)遇,優(yōu)美生態(tài)產(chǎn)品、優(yōu)質(zhì)公共服務(wù)和優(yōu)良生活環(huán)境是新城新區(qū)發(fā)展的前提。
把優(yōu)質(zhì)的公共服務(wù)搞好了,把高效率的長(zhǎng)距離交通出行服務(wù)建好了,就抓住了“產(chǎn)業(yè)資本跟著人才走,人才跟著公共服務(wù)走,哪里更宜居,知識(shí)分子就選擇在哪里居住,知識(shí)分子選擇在哪里居住,人類的智慧就在哪里集聚。”這一數(shù)字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城市化的底層邏輯。比如深莞之間松山湖與華為,廣佛之間北滘的格力等新業(yè)態(tài)就自發(fā)而生。
按照“住和行”關(guān)系的新認(rèn)知,高品質(zhì)居住的用地提供主要在外圍的新城新區(qū),新城新區(qū)持續(xù)推進(jìn)以軌道交通為代表,以及現(xiàn)代化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TOD與公共服務(wù),隨著外圍新城新區(qū)業(yè)態(tài)的發(fā)展豐富完善,將從根本上將“單向交通”轉(zhuǎn)變?yōu)椤半p向交通”,也是治理大城市病、提高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運(yùn)營(yíng)效率的“妙招” 。
這也就真正建設(shè)起來(lái)了軌道上的都市圈和城市群,也會(huì)促進(jìn)在都市圈和城市群層面集聚優(yōu)質(zhì)創(chuàng)新要素,從更大空間配置上創(chuàng)新資源,充分發(fā)揮創(chuàng)新要素集聚和輻射效應(yīng)。
“政府和市場(chǎng)關(guān)系”的新認(rèn)知
無(wú)論是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jì)體系建設(shè)還是一二三產(chǎn)深度融合,區(qū)域協(xié)同還是城鄉(xiāng)融合,都市圈和城市群發(fā)展,還是在推進(jìn)各項(xiàng)改革的關(guān)聯(lián)性、系統(tǒng)性、整體性、協(xié)同性方面,都需要從單打獨(dú)斗到深度合作協(xié)作,都需要回到如何“從分到合”。那么政府怎么做?市場(chǎng)和企業(yè)怎么干?
從推動(dòng)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戰(zhàn)略以來(lái),總書記多次叮囑各地,“自覺(jué)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 可見(jiàn)區(qū)域協(xié)同中政府之間“一畝三分地”這一現(xiàn)象不僅在京津冀存在,在各個(gè)地區(qū)都是存在的。
目前在政府協(xié)作之間的“一畝三分地”、各個(gè)政府部門合作之間的“爭(zhēng)權(quán)奪利、推卸責(zé)任”是客觀存在的。
對(duì)于企業(yè)和市場(chǎng)發(fā)展來(lái)說(shuō),比如一家有國(guó)際影響力的企業(yè),他不能只考慮給所在的城市這“一畝三分地”提供好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還要給全國(guó)提供服務(wù),乃至要考慮給全球提供更好的服務(wù)。今天企業(yè)和產(chǎn)業(yè)大量的創(chuàng)新都來(lái)自于跨界,來(lái)自對(duì)既有規(guī)則的顛覆,企業(yè)家尋找區(qū)域協(xié)同、產(chǎn)業(yè)協(xié)作中各種產(chǎn)業(yè)、產(chǎn)品、服務(wù)之間的痛點(diǎn)、斷裂帶,建立新的連接、新的協(xié)同,從而實(shí)現(xiàn)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創(chuàng)新,這才是創(chuàng)新的起源。
對(duì)政府來(lái)說(shuō),恪守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原理,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和城市發(fā)展過(guò)程中因勢(shì)利導(dǎo)地提供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所需的公共服務(wù)與社會(huì)管理,有所為有所不為,才是破局“一畝三分地”實(shí)現(xiàn)“從分到合”的基本邏輯。解決好新認(rèn)知,需要各級(jí)政府各個(gè)部門都要強(qiáng)化自我革新的意識(shí),突破思維慣性。
探索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和城市化在新發(fā)展階段的新發(fā)展邏輯,需要解決好“業(yè)和人”、“城和鄉(xiāng)”、“住和行”、“政府和市場(chǎng)”這四組關(guān)系的新認(rèn)知。因?yàn)檎J(rèn)知的邊界,就是人生的邊界,一個(gè)人一生的成長(zhǎng),就是認(rèn)知的持續(xù)提升,財(cái)富也是對(duì)認(rèn)知的標(biāo)定,人如此,城市也是如此。
未來(lái)具備全球影響力的城市是靠思想而不是“實(shí)物”繁榮起來(lái)的,而使它獲得成功的是從面對(duì)面接觸和人際網(wǎng)路中產(chǎn)生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將人的大腦與其它大腦集中在一起,激發(fā)思想、藝術(shù)和社會(huì)變革,人才能演化為一個(gè)完全的城市化物種。這才是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最重要的創(chuàng)新生態(tài),也是我國(guó)城市化未來(lái)最大的發(fā)展空間。
(作者為中國(guó)城市中心總工程師,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編輯:王延春)
- 免責(zé)聲明
- 本文所包含的觀點(diǎn)僅代表作者個(gè)人看法,不代表新火種的觀點(diǎn)。在新火種上獲取的所有信息均不應(yīng)被視為投資建議。新火種對(duì)本文可能提及或鏈接的任何項(xiàng)目不表示認(rèn)可。 交易和投資涉及高風(fēng)險(xiǎn),讀者在采取與本文內(nèi)容相關(guān)的任何行動(dòng)之前,請(qǐng)務(wù)必進(jìn)行充分的盡職調(diào)查。最終的決策應(yīng)該基于您自己的獨(dú)立判斷。新火種不對(duì)因依賴本文觀點(diǎn)而產(chǎn)生的任何金錢損失負(fù)任何責(zé)任。





 新火種
2023-10-27
新火種
2023-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