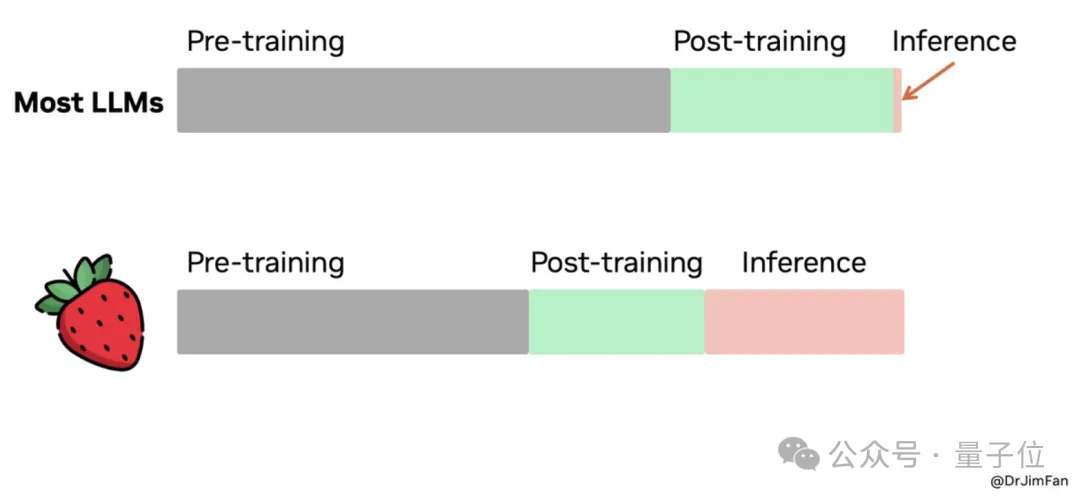AI徹底火了!地下850米最新實探大模型如何在礦井下運行?
提及煤礦,很容易令人聯想到礦工的滿面烏黑、“悶熱”“潮濕”的工作環境、甚至時而發生的礦難……在過去,這是眾多煤礦的真實現照。然而如今,一切正在變化,變量則來自于“AI大模型”。
自ChatGPT帶火整個AI賽道后,國內大模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已有93個大模型公開發布,逐漸形成“百模大戰”之勢。
以ChatGPT為代表的通用多模態大模型在問答、寫作、作詩方面展現了“驚艷”的一面,但隨著市場回歸理性,人們不禁要問:大模型除了聊天、創作外,還能干些什么?
截至目前,已經有不少科技巨頭將目光投向B端。華為近期發布了“不作詩,只做事”的盤古大模型3.0,聚焦行業場景、垂直領域;曾經試圖對標ChatGPT的百度文心一言也將視線轉移至能源、汽車制造等領域;騰訊云也試圖做行業大模型解決方案。
近日,中國基金報記者實探了位于山東西南部的多處煤礦。其中最深的礦井位于菏澤市巨野縣的新巨龍煤礦,其開采深度達到810米至950米,這有如將全球最高樓迪拜哈利法塔向下倒砌。
而記者在實探的掘進工作面位于地下約850米處,乘坐罐籠(礦井中的升降電梯)下到礦底,足足需要三分鐘時間。而在暗無天日的礦下駐足數小時,時間仿佛都在加速。
值得注意的是,先于記者下礦井的,還有AI大模型。那么,AI大模型如何在地下超800米之初,改變煤礦人的作業方式?如何與礦山開采發生“化學反應”?
大模型如何在礦井下運行?
“在我剛畢業的時候,煤礦每年的事故率在5%左右,礦工一直是高風險工種,”山東能源黨委常委、副總經理劉健對記者坦言。在他看來,“如何留住人”一直是煤礦企業需要解決的棘手問題,如何讓更少的礦工面臨高風險,是行業內部重點研究探討的問題。
通過何種方式可以讓更少的礦工下到礦井中?如何讓井下工作時間縮短?
記者日前實地走進了新巨龍煤礦,該礦是山東能源魯西礦業旗下主要煤礦之一。新巨龍煤礦于2004年6月份開工建設,2009年底投產運營,礦井核定生產能力600萬噸/年,保有資源儲量10.8億噸。據工作人員透露,該礦至少還可開采47年之久。
記者換上礦工的裝備后,乘坐罐籠經過近3分鐘下到地下約850米的礦井內。隨后,記者又換乘通勤車在如地下迷宮般的隧道內穿梭。
從出罐籠到抵達掘進工作面,通勤車足足開了約半小時。據新巨龍工作人員介紹,這段車程行駛距離超過10公里。很難想象,在超800深地下,還盤踞著如此龐大的地下網絡。而下車后,仍需要步行數百米,才能真正達到掘進工作面(如圖),整個過程猶如“地心歷險記”。
掘進工作面(來源:山東能源現場拍攝)
不過,與想象中不同的是,礦井中并沒有出現粉末飛揚的場景,相反是一系列設備井然擺放。整個路程中,僅看到為數不多的幾位工作人員作業。同時,每隔一段距離就能看到攝像設備、無線基站等設備。
礦下設備擺放(來源:山東能源現場拍攝)
據新巨龍煤礦副總經理牛永明告訴記者,國內煤礦的煤層普遍較深,開采難度相較于國外難太多,“比如在澳大利亞,多數煤礦是露天礦,完全不需要下地采掘。”
據他介紹,在深入地下的煤炭采掘過程中,沖擊地壓是造成煤礦塌陷最主要因素,是需要防范的最大風險。而中國是世界煤炭行業受沖擊地壓影響最深的國家之一。
如何化解這一風險?鉆孔卸壓工程成為沖擊地壓防治的主要手段。記者在現場也觀察到,鉆孔機器是掘進工作面所必備的設備。
采煤工作面(來源:山東能源現場拍攝)
上述人士介紹,在采煤過程中,巖體應力猛烈釋放會導致事故,通過對巖壁打孔產生一定空間,可以令巖壁壓力向孔內釋放,從而避免向采煤隧道內擠壓。因此,在卸壓鉆孔施工時,人員操作不當,比如深度不夠、角度錯了等,會影響卸壓效果,繼而導致安全隱患甚至事故。
其中,鉆孔深度是防沖卸壓工程最關鍵的參數之一。記者在鉆孔卸壓工作面觀察到,鉆孔機器上安裝著高清攝像設備以及其他相關傳感器設備。據牛永明介紹,AI大模型可對鉆孔施工情況進行實時監測,可實現鉆孔深度自動核驗、孔深不足及時提醒,避免漏檢、遲檢,減少人工核驗工作量。
地面實時監控卸壓打孔(馮堯攝)
“過去,我們在檢查礦工作業的規范性方面,通過執法記錄儀對打鉆的全過程錄像,錄像完成后再帶出礦井,再由專人對視頻進行核查,也就是說視頻現場如果拍了一個半小時,那地面上的人就要看一個半小時,非常耗時耗力,”新巨龍煤礦防沖中心主任賈海濱直言。
而大模型下地之后,地上工作人員通過AI大模型視覺識別能力來識別礦工是否打鉆達標。據記者隨后在地上指揮中心觀察,盤古大模型通過前期學習,可以準確識別包括礦工、設備在內的各種井下物件。當礦工操作不規范時,可第一時間作出提醒,極大降低了溝通的時間成本,同時降低了防沖工作風險。
采煤工作面液壓支撐(來源:山東能源現場拍攝)
據賈海濱透露,“過去一個鉆孔卸壓小組需要14-16人左右,而現在僅需要4-5人即可。而在地面,1位地上人員可以監測5、6個工作面場景。”
他介紹,用了AI識別后,一是增強了實時性,從之前隔天核驗到現在現場完成核驗,卸壓孔深度不足時系統及時提醒,沖擊地壓監控中心可實時查看井下工程施工情況,發現問題及時整改。二是減少了人工核驗工作量,從之前人工審核一個卸壓鉆孔耗時15分鐘到使用AI后人工審核時間降低到3分鐘,降低人工核驗工作量80%。
大模型賦能產業的縮影
記者在新巨龍煤礦礦井中所見的景象,也僅僅是大模型運用于采礦工作場景之一。大模型另一個場景是選煤環節,選煤過程中避免粗顆粒物進入介質回收環節,是保證選煤效果的關鍵因素。
記者李樓煤礦看到,為解決“跑粗”發現不及時難題,該礦通過在稀介桶內加裝截粗裝置和攝像儀,在邊緣推理設備上部署AI模型,實時分析截粗裝置上的粗顆粒物堆積情況,及時告警提醒,同時推送證據圖片,以幫助巡檢人員處置,降低工人勞動強度,從而提升選煤效果。
地面監控中心(馮堯攝)
李樓煤礦同樣是山東能源魯西礦業公司權屬礦井之一,這里優質稀缺煉焦煤地質儲量達10.8億噸,可采儲量1.78億噸,年核定生產190萬噸。
另外在鮑店煤礦,該礦也全工藝段采煤機記憶截割、液壓支架自動跟機、自動找直、時序自動放煤、煤流智能調速、運輸機自動張緊和斷鏈保護等功能保持常態化運行,極大改善了職工作業環境,提高了礦井安全保障水平。
而上述AI大模型之所以能夠“下礦”,要得益于山東能源、云鼎科技依托華為盤古礦山大模型的開發。據華為煤炭軍團CEO蔣旺成透露,盤古礦山大模型主要涵蓋采煤、掘進、主運、輔運、提升、安監、防沖、洗選、焦化9個專業21個場景應用。
在細分領域,包括勞動保護用品穿戴規范性監測、人員乘坐架空乘人裝置規范性監控、人員誤入危險區域及關鍵崗位行為狀態監護、煤礦限員AI監管分析等也均是大模型“發熱”的場景。
那么,大模型何以能在煤炭行業落地?用蔣旺成的話說就是,“智能化程度越低、人員需求越大的行業,往往是AI大模型賦能空間最大的行業。”
在煤炭行業中,不少煤礦早期采用傳統的人工巡檢方式,作業現場多是高溫、高危、粉塵、潮濕等惡劣環境,初期采用攝像頭遠程監控系統,但是需要大量的人力來觀看視頻發現異常點,且無法完成海量視頻異常標注和識別。
在山東能源黨委常委、副總經理劉健看來,煤炭行業最應該實現智能化,讓機器設備代替人工。他認為,作為企業而言,希望借助大模型視覺能力實現皮帶運輸、防沖泄壓、人員安全、流程合規檢查等場景的智能化監測和識別,以大幅降低人力監測工作強度。
早在2020年2月,國務院八部委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快煤礦智能化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將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與現代煤炭開發利用深度融合。
而在2022年8月,科技部發布《關于支持建設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應用場景的通知》,明確提出促進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和支持以智能礦山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應用場景工作。
實際上,政策接連出臺也為大模型“下礦”提供支撐。據了解,山東能源在國內外共有85處煤礦。自2021年以來,該公司已投入100多億元進行礦井智能化建設,建成了133個智能化采掘工作面、24個5G+智能礦山應用場景,9處國家級智能化示范礦井全部通過驗收。
根據規劃,“十四五”期間,山東能源還計劃投入資金300億元,建成一批多種類型、不同模式的智能化礦井。“目前集團已建成300多個智能化采煤工作面,智能開采產量占比超過80%。煤礦智能化工作開展以來,累計減少井下作業人員1.2萬人,”劉健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大模型能夠實現“下礦”,合作模式也是不容忽視的環節。早在2022年1月,山東能源、云鼎科技、華為三方聯合成立了聯合創新中心,三方依托盤古大模型建設了人工智能訓練中心,實現了中心訓練、邊緣推理、云邊協同、邊用邊學。
換言之,山東能源提供商用場景、華為提供盤古大模型的底座,而云鼎科技基于盤古大模型底座,承接人工智能訓練中心場景落地任務。實際上,該模式也給市場提供了一個大模型商用路徑的模板。
在華為方面看來,能夠擁有落地場景作為試點平臺,對于大模型產業落地至關重要。蔣旺成對記者直言,過去阻礙大模型商用的最大阻力其實是兩端存在難以突破的隔膜,即“打造大模型的科技類公司了解大模型,但卻對商用行業不甚了解;而商用的行業人士對所處的行業了解,卻不懂大模型”。
頭部玩家才能享用大模型?
隨著市場對于大模型的態度日益理性,能否應用落地并且具備商業化能力,逐漸成為檢驗大模型成功與否的標準。業內普遍認為,不同于傳統C端消費互聯網,B端產業才是大模型的主戰場。
此前,華為盤古大模型已經明確表示“不作詩、只做事”,而曾經試圖對標ChatGPT的百度文心一言也將視線轉移至能源、汽車制造等領域;騰訊云宣布做行業大模型解決方案;科大訊飛的星火認知大模型也將包括汽車、教育作為“降落點”。
浦銀國際一份研報認為,行業大模型或成為衍變趨勢。該機構認為,未來大模型會進一步分化為通用、專用和特定場景,通用大模型并不能解決很多企業的具體問題,而模型的大小,主要還是取決于企業用戶的自身需求,企業的大模型應用需要綜合考慮行業專業性、數據安全、持續迭代和綜合成本等因素。
不過,從目前來看,AI大模型在B端商用仍處于在探索階段的初期,仍面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以煤炭為例,當前能夠為AI大模型提供商用試驗場所的,局限于行業的大型頭部企業。
首先,盤古大模型之所以能夠“下礦”,一個不容忽視的前提是山東能源前期投入大量財力物力,已經初步完成其煤礦的“數字化改造”,并能實現數據互通。簡而言之,便是數字化改造“第一步”,大模型上路“第二步”。
“我們曾經遇到一處煤礦,井下就有超過20種系統,操作起來非常復雜,”華為礦山軍團一位相關負責人對記者直言。該人士所提及的礦井中,設備所使用的基本國外廠商系統,均處于封閉狀態,互不通信。而且外方供應商非常強勢,并不開放數據接口。在這種狀況下,AI大模型穩定運行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新巨龍煤礦方面也側面印證了上述說法。據新巨龍煤礦相關負責人透露,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曾面臨礦山、裝備和通信數據編碼不統一、通訊接口不兼容、傳輸協議不開放、系統集成難度大等突出問題。“光打通數據接口,實現數據共享就花了兩個月時間,”該人士稱。
而且,據其透露,要實現大模型運行,底層生產系統的基礎條件要具備。比如,需要的傳感器要齊全,要使用高可靠性的裝備;在架構上,按照工業互聯網架構來設計信息化系統。
事實上,僅僅是完成數字化改造,便需要耗費大量財力物力。從國內企業已推進數字化轉型所處的階段來看,大多數企業還處于轉型初級階段,已完成數字化轉型的企業為數不多。
也就是說,目前來看,將大模型實際運用于商業場景,更像是頭部玩家的“游戲”。
在業內看來,煤礦智能化建設本身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復雜的自然環境,想要真正實現智能化非常困難。在記者采訪的多位人士看來,要真正全面、系統實現智能化升級,還需從網絡、平臺、標準、人才培養等多個領域統籌兼顧、協同推進。
華為方面也提及,目前AI大模型在行業中落地過程中,各項參數目前缺乏明確統一標準,“比如大模型的判斷,精確到什么程度,目前是根據各個試點企業實際需求出發。”該人士也提及,未來需要更多企業加入進來,便會逐漸形成生態,行業標準設定才會進一步規范。不難看出,AI大模型的行業落地長坡厚雪。
(文章來源:中國基金報)
- 免責聲明
- 本文所包含的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看法,不代表新火種的觀點。在新火種上獲取的所有信息均不應被視為投資建議。新火種對本文可能提及或鏈接的任何項目不表示認可。 交易和投資涉及高風險,讀者在采取與本文內容相關的任何行動之前,請務必進行充分的盡職調查。最終的決策應該基于您自己的獨立判斷。新火種不對因依賴本文觀點而產生的任何金錢損失負任何責任。





 新火種
2023-11-03
新火種
2023-11-03